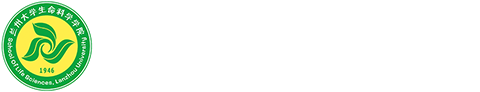时间:2014年10月20日9:20
地点:兰州饭店
人物:贾敬芬
采访人:王秋林
摄像: 红叶
文稿摘录整理:屈言雪(学生志愿者)
宋欢予(2015级萃英学院数学班学生志愿者)
王:贾先生,您好。学校档案馆从2012年3月份开始,一直推进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就是请老先生回忆自己所经历、了解的兰大(同时也收集相关的实物档案资料,照片、笔记、讲义、证章、书信等),这些将作为历史资料在档案馆里永久保存,成为后人了解、研究兰大的资料。今天请您给我们做个回忆。
我是老兰大
贾:我是1957年考到兰大生物系植物专业的,那时是五年制。到了1962年大学毕业后,考了研究生,成为郑国锠先生第一批研究生。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直到1967年才发研究生毕业证。我被分配到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我在那里工作到1970年底。到1971年元月份以后又作为教职工调来兰大了,一直待到1996年;只有中间两年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瑞士。所以我是老兰大的学生,也是老职工。调到兰大来主要是因为丈夫王勋陵(原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在这儿工作。
1957年冬天参加过引洮工程,在西果园修水渠,1958年去西固建自来水厂时挖土方,打地基。1958年秋冬,去甘南舟曲原始森林藏族区参加大炼钢铁。
从1957年到1959年,我们那届学生遇到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特别是几门化学课、植物学、分类学的老师。1960年到1962年,这个时候已经是生活困难时期了,天天挨饿,班上得浮肿的男同学不少,我甚至也得了半年肺结核。但是,那三年还是能够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开会少了,也没有多少体力劳动。可以说大学阶段的专业基础是在后三年打下的。那时饿着肚子也学,好像也没有什么怨言,因为全国的形势都那样。我分配学植物学专业,我们每年暑期都有野外实习,前三年暑假曾到过兴隆山,麦积山,陇南山区。后两年去民勤治沙站实习,学到了不少感性知识。
江隆基印象
1959年江隆基校长调到兰大,那时我是大三学生。江校长是一位高水平、很有魄力,深受尊敬的教育家。他那时常在饭厅二楼作报告,全校的师生都来听。我记得那时听说江校长要作报告,我们学生都异常兴奋,非常喜欢听他作报告。我感到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大学和研究生时期遇到了这样的好校长。江隆基校长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坚守政治原则,是很有魄力的教育家。他来了以后整顿教学秩序,纠正左的倾向,积极调动受压抑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师们的积极性,使得兰州大学面貌一新,走上了正常的教学轨道。我们大学后三年能踏踏实实学些专业知识,也得益于江校长来后建立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兴起的良好学风。兰大的好校风延续至今,与江校长时期打下的基础很有关系。好的校风、学风使得兰大的学生具有勤奋、刻苦、和务实、好学的特点。兰大虽然地处西北,条件很差,但我们学校却在国内外有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大学毕业后就成为了郑国锠先生的研究生。在良好的学风环境中,大家能认认真真读书做学问。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细胞学,还补休了遗传学及高级生物化学。郑先生为我和另一位师兄选了植物细胞化学作为研究方向。正是在研究生阶段,郑先生把我们引向了做科学研究这条路上来。在文革期间我被分配到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工作。
和郑先生一起搞科研
我1971年调到兰大时还处于文革阶段。没有学生,没有教学。当时生物系在办工厂,我被分配洗瓶子。还有几位外系的老师都在我们生物系劳动。记得林迪生校长,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蔡寅老师也和我们在一个大教室里一起洗瓶子。

1985年贾敬芬在实验中
大约在1971年秋,军区被服厂有一个任务交给学校,说是部队的皮大衣太重,想想办法用微生物脱油脂减少重量。由生物系郑先生牵头,组织几位老师做这项工作,我也在其中。从皮大衣里面分离了好几种菌,进行微生物发酵,然后提取脂肪分解酶,筛选脂肪酶活性高的菌种。我承担酶的提取、活性分析、检测等。那一段时间和郑先生一起做这项研究,觉得好容易有机会进实验室做实验了,所以过得特别愉快。目的明确,而且不断有进展。还获得了活性较高的脂肪分解酶,筛选出了几个好菌种。
其实在文革期间,郑先生还是在关注着国内外在细胞学方面发展动态。虽然没有教学,没有什么课题任务,但听仝允栩先生说过,他依然在家里留意着专业书和杂志。那时候我们几乎不看业务书,谁都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但是郑先生还是能稳住,比我们头脑清醒。大概是在1972年,他就提出做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这是国际上兴起的一种育种新技术,中科院有的单位已着手搞起来了。郑先生倡导下,由杨汉民几位老师就开始了小麦花药培养,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取得很好的结果,还带动了后来的教学和学生培养。
到了1973年,国际上兴起了一项热门课题-原生质体培养,即把植物细胞壁去掉,游离出裸露的原生质体,经过培养后再生新壁、再分裂,再长成植株。这种技术的目标就是进行体细胞杂交和导入外源基因;因为在没有细胞壁的阶段,可以诱导原生质体融合,这种融合可以在种间、属间、甚至在科间进行,从而产生远缘体细胞杂种,克服有性杂交不亲和性。因为没有细胞壁的阻挡,原生质体可以摄取外源DNA,获得缘远转基因杂种。原生质体培养是这些研究的基础。
这项工作就由我来研究。当时觉得很深奥,高不可攀。我们从来没有操作过活细胞,要用的特殊药品,纤维素酶和果胶酶也买不着。那时也没有立课题,只是想试试。没有无菌操作设备,就找木匠用三合板做了个木头箱子,前面挖两个洞,可以把手伸进去,里面安上紫外灯管,加上酒精灯,算是无菌操作箱。这样实验勉强可以做,但是操作单细胞还是经常染菌。买不着酶,就从上海植物生理所要来他们分离的菌种,自己进行培养发酵,提取纤维素酶。除了培养基有各种化学成分外,还要新鲜绿色稻草,兰州这里又没有,到处去找。没有冰箱、低温设备,提取酶就只能在大冬天把窗户打开,使得房间变得很冷。提炼的酶并不纯,勉强能用,就这样我们开展了原生质体分离和培养工作。
我们还是在国内高等学校里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那时开展原生质体培养的单位只有五个,科学院的四个,高校就我们一个。后来1978年以后,搞这一领域的单位就多起来了。所以郑先生指点的这一科研方向还是紧跟了国际前沿。
郑先生有一个从事一生的研究方向——植物的细胞核染色质穿壁转移现象及其机理研究。这项研究他从美国回来就开展,该课题搞了五六十年,在国内外细胞学界,还是很有影响的。他和国内做类似研究的老专家吴素萱、娄成后用的实验材料不同,研究角度也不同。郑先生先用兰州百合的生殖细胞做这个实验。后来观察了几十种不同科属的植物,发现很多植物都有这种现象,他首先提出“染色质穿壁在植物界具有普遍性”。接着从显微、亚显微,细胞化学的方法,研究穿壁过程中核酸、蛋白质、酶的活性的变化,从而进入到机理方面及其生物学意义的研究。后来用上了分子生物学手段,把这种现象机理研究得比较透彻。有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Protoplasma上面。
王:郑先生也曾说到有两篇比较有影响的论文,这就是其中之一吗?
贾:是的。郑先生看准哪个方向,觉得它值得深入,坚持下去必有成果,另外也绝对不要忘记开拓性的领域。这也使得我们兰大细胞学在全国占上了个位置。我感觉到郑先生对两件事情很敏锐的。
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在“四人帮”打倒以后,就要大学招生了,当时国内没有统编教材。1978年教育部召开有关编写全国统编教材的工作会议,当时在教务处工作的赵松岭代表学校出席,踊跃揽了这个差事。郑先生愉快地承担了编书任务。用了两年时间编成并出版了《细胞生物学》这本书。因为国内从未有《细胞生物学》的教材版本,这又是一门进展很快的学科,必须把这些年来的新成果、新进展反眏在书里,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郑先生有这种底子啊,因为他一直关注着国内国际在这方面的发展。记得第一版八十多万字,收集大量的资料,也有国内一些著名专家帮忙,如仝先生、北大的翟中和,医学科学院的薛社普,东北师大的郝水教授等,给他提供了不少资料,有的还编写了章节,国内、外专家也提供了不少图片。这本教材是我们国家第一本《细胞生物学》统编教材,影响很大,因为大家都没有教本嘛。后来陆续出现了其他高校的老前辈编写的细胞生物学教材,相对都比较晚。
还有一件事就是,国内老专家们酝酿,决定成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由郑国锠先生出面张罗组织,1980年在兰州召开了“全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成立大会,细胞生物学届的老前辈全都来了。学会理事长是由上海细胞所的庄孝僡所长担任,郑先生是副理事长。我当时在瑞士,没有参加成立大会。等我回国以后,到1983年开第二届大会,就把我选为理事了,第3届后来又选为副理事长,一直到第七届。从1980年到现在,三十几年了,四年开一次全国大会。由于我们兰大是发起单位,由郑先生领导的细胞生物学团队有一定的实力和基础,这就给我们两个理事名额。我在学会的活动中认识了很多同行学者,年年开会,学术交流,也通过学会了解国内外的很多动态,很是受益。
王:也扩大了兰大的影响。
贾:是。兰大地处西北,学会还让我们来带动西北。那时候青海、宁夏、新疆一个会员都没有,学会还让我们来带动,在西北发展会员。所以我觉得郑先生在推动学会活动上是有贡献的。
这两件事情在全国都很有影响。
郑先生把我引上了科研之路
贾:我是郑先生的老学生,跟我同届的还有王义琛,我的师兄,那是第一次招研究生。做研究生阶段,条件也差,只能做些传统的显微切片,进行常规细胞结构观察。但是他也是让我们两个尽量扩大眼界,让我们从细胞学、胚胎学的角度,看看一些植物受精前后的细胞化学成分的变化。我跟师兄两个就这么观察了三十多种植物,有栽培植物,包括小麦、大麦、燕麦,和野生植物。从开花授粉、胚囊的发育、受精,一直到胚胎形成。我们都做好多切片,做各阶段DNA、RNA、蛋白质、淀粉等成分在植物不同发育过程中的变化研究。总之我们得到了很多训练,在科研能力上有很大提高。
总之,兰大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作为青年教师,郑先生把我们引上了科研之路。
郑先生有一副威严相。我们几个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把我们抓得很紧,我们也很自觉,假日几乎没休息过,有时候晚上还要做实验。我记得大年三十我们都干到了下午六点钟,郑先生把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有聂秀菀、杨庆兰请到他们家去吃饭,有说有笑。其实郑先生有很和善的一面。

贾敬芬王勋陵夫妇和郑国锠一起参加全国学术会议
我做原生质体培养实验,几乎天天和郑先生讨论。他看到什么文献就给我介绍,我们配合得很好,还一起到国内参加学术交流。1975年到山东农学院交流,他就把我和师兄带过去。后来在1985年,江苏农科院遗传生理室的奚元龄老先生,邀郑先生讲原生质体培养,郑先生也还是把我推到前头,一同给他们讲。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老先生对我们年轻教师的用心培养。
王:聂秀菀一直在做这个实验工作?
贾:嗯,聂秀婉一直是做染色体穿壁方面的主力,从事显微和超显微,技术精湛,后来也用上分子生物学手段。她始终是兢兢业业的。她和杨庆兰是郑先生染色体穿壁课题研究的主力。后来学校买了电镜,也主要是为郑先生做这个染色体实验的。
王:那个电镜室就是专门为他建立的?
贾:当时是的,还配备了学物理的几位老师作为电镜室专职人员。后来电镜室也对外了。所以成就郑先生的工作,也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这个细胞室文革后就形成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染色体穿壁课题,另一个是植物细胞工程,包括组织培养、原生质体培养、体细胞融合、遗传转化等。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技术也都建立起来了。
王:在细胞生物学方面,我们兰大在全国也应该是有地位的。
贾:是的。不过我们毕竟还是条件差一些,得力的人手还是少,资金有限,设备差。全国东边的一些大学,特别是中科院一些研究所发展很快,迅速走在了前面。不过我看到今天的兰大,分子细胞生物学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新团队,工作很出色,高水平成果不断。这是很值得庆幸的。
去瑞士作访问学者
改革开放带来了公派出国深造的机遇,我是幸运者。经学校的英语和专业测试,我被选上了。我的英语底子差,大学、研究生阶段学的俄语多,只是研究生时作为第二外语学了英语。出国前先到西安外语学院培训了一学期,主要是口语和听力。1979年10月就出去了。
当时英语国家没名额,与郑先生商量,去了瑞士。瑞士巴塞尔市有一个国际很有名的研究所(Friedrich Miescher Institute),那里植物细胞工程和遗传操作处于领先水平。

1979年在瑞士实验室作访问学者
经与联系去了Ingo Potrykus实验室。那里官方语言是德语,我不懂,但学术交流用英语,对我来说,语言仍然是最大障碍,很影响交流。幸运的是,我们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原生质体培养,工作基础和这个实验室做的研究范围很贴近,加之去以前,参阅了他们发表的一些文章,对他们的工作范围有了一些了解,所以语言上的障碍没有带来太大困难。那时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主要有原生质体培养和体细胞杂交。在那里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实验室条件特别好,我不仅做原生质体,而且做体细胞杂交,还做了外源基因的导入。
我在那儿待了整两年。虽然人家每周是休息两天,我每个周六都要去实验室做实验,有时星期天也去半天。周末实验室都没有人,条件那么好,药品随便用,也不用洗东西,都是一次性的。这么好的条件,当然得抓紧利用。
我在那儿的两年,实验很有进展。第一年用两种植物材料获得原生质体培养再生植株,还发表了文章。第二年与搞突变体筛选的实验室合作,做体细胞杂交,是拿两个不同属的植物原生质体做杂交,获得了成功。另外还做了原生质体的遗传转化。当时国际上1980年只有七十种植物原生质体培养取得成功,我们的是其中一个。另外做体细胞杂交,属间体细胞杂交只有五例再生植株,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在1981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我也参加了。德国老科学家在作综述报告中,把我们体细胞杂交的例子举了出来。那是在瑞士做的。遗传转化方面的工作是用矮牵牛原生质体做受体的,最后成功了。用原生质体做受体进行外源基因导入,当时国际上只有两例。
我那个指导老师Potrykus非常善良,那是个德国人,一直在瑞士工作,在原生质体遗传操作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多年了,我回来后仍和他保持联系多年。后来他到了苏黎世去了,做水稻转基因。针对非洲儿童维生素A的缺乏症,他的团队把维生素A的编码基因转到水稻里,获得过量合成维生素A的黄金水稻。该研究仍然有人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继续做。
在我的科研道路上,郑先生把我们引进了门,教给我们思路,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掌握了专业技能,真正走上了科研道路。在瑞士那里工作时,才不感到生疏,才能做出了一些结果。我的文章也是从1980年以后才开始出的。在此之前没什么文章,也就只有一两篇。
回来以后做的方面就多了,加上研究生,本科生。现在有二百多篇文章,当然多是指导研究生搞的。培养研究生,要求他们有文章。他们应是第一作者,我多作为通讯作者,我绝对是这么做的。在瑞士,人家那个导师也是这样,外国人很讲究这些,谁做的谁打头。

1992年贾敬芬正在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从原生质体培养开始做起
贾:在出国之前,我们就开展了原生质体培养。虽然技术上得到磨炼,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走了死胡同,用的材料不合适。当时认为小麦是粮食作物,从叶片很好分离原生质体,就选了小麦叶片作材料,培养可以活很长时间,偶然分裂一次,但是不能持续,始终不成功。国内外很多单位都曾用过小麦叶片作材料,均未获得到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直到现在这个难题也没突破。可见我们最初用的材料不合适,走了弯路。不仅是小麦,就是禾本科植物的叶片原生质体培养,到现在都没有突破。后来国外学者采用幼胚,受精以后半个月的幼胚进行培养,先获得胚性愈伤组织,再来分离胚性原生质体。这种原生质体就可以持续分裂再生成植株。我们生科院郭光沁教授在山东大学工作时,在这方面也曾获得成功。以后人们搞小麦原生质体培养就是走这个路子。
我从国外回来以后,继续在我们细胞室开展这一方向的研究。条件简陋,经常污染细菌,实验效率很低。然而,当时已经开始可以买到一些商品酶了,有一点点钱,买国外产的纤维素酶、果胶酶。研究工作使用了更多的植物作材料,逐渐就把我们这个实验室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了,研究生们多开展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到了1984年国家分配来了两个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的进修教师,指定在我们实验室工作,也都四十多岁了。冲着他们,学校给钱购置了超净工作台,先做组织培养,练习无菌操作技术,接着就做原生质体培养。一个人做的是当归,另一个做胡萝卜。作了一年,做过八十几次实验,几乎都是染菌的。他们期限到了,他们的原生质体刚刚有点儿分裂。走的时候说,回去要汇报交代的,叮咛我,以后写了文章要把他们挂到头里做第一作者。接着我就继续给他们培养,把当归原生质体变成了愈伤组织,但已经算很成功了。胡萝卜也得到了植株。写成文章把他们挂了第一作者,登在了科学通报上,成全了他们,那时候友好嘛。这样也算培养了两个朝鲜进修教师,这是1984-1985年的事情。
带动西大生物技术学科建设
王:那么您后来怎么又到西安去了?
贾:大概在1994年秋天,西北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和一位校长助理来到兰州,没有住在兰大。我突然接到他们的电话,约我去到他们的住处,动员我去西大。当时西大生物系师资较少,教职员工50多人,学校也正在作着进入211工程的准备,另外他们想发展植物生物技术,已经向上申请建立植物生物技术实验室,但没有人牵头。动员我去西大。同时,那里的植物学专业博士点将面临评估检查。他们的博士点只有一个导师,成果显得分量不够,方向比较单一。领导们着急,就来动员我去那里。
后来1995年春又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副系主任来兰州做第二次动员。我是在关中长大的,很喜欢西安那个地方,而且我的两个妹妹都在那边,就动了去的念头。但1995年冬天我得了一场病,住院好几个月,本也不想调工作了,可系主任又来兰州,劝我到西安去,说西安医疗条件好,给我治病,让我很受感动,就答应了。
到那儿去后,条件很差,没有人,生物技术方面还是空白。从建实验室开始,开始招研究生,组建了陕西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也壮大了植物学专业博士点的导师队伍。在评估检查中,我的材料和王勋陵兼职的材料都用上,西大的博士点检查就通过了,算是起了很大作用。
王:那您和王先生一起到西北大学?
贾:不是,那时候他还当着系主任,根本没有提出来调动,只是在西大兼职。在西大那边,西大也把他抓住,一般的兼职教师也不带任何教学科研任务,可是就让他招博士,带动西大生态学的发展。西北大学的生态学,实际上也缺人。王勋陵的系主任届满后,不定时地去西大,招了好几届研究生,还多次申请到国家基金和省课题,对西大的生态学发展起了带动作用。后来生态学已经成一级学科,西大已经有了生态学科博士点。
王:我们学校到西北大学去的几位老师,把这个摊子带起来了。

1993年贾敬芬和研究生一起在现场讨论
回忆王勋陵
王:还有请把您和王先生的情况说一下。
贾:我和他相识相处了四十多年,在我印象中,他对事业非常执着,为人又非常实在。他比我脑子灵活,肯动脑筋,有某些方面的聪明才智。他不大跟人开玩笑,就是干实事,就这么个人。说话绝对是直来直去,对老师、对领导都是直言,所以有的领导不喜欢他。他还敢给领导提意见,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1975年领着植物专业的学生在一条山农场劳动,还顶撞过领导说:让学生整日开荒劳动,是误人子弟。
他当生物系系主任期间,哎呦,那整天琢磨怎么给系上办好事。一上来就面临各个系都在想尽办法提高一下大家的生活,能够增加点什么收入。化学系靠仪器运转能够有点收入,我们生物系,就在生物园后面临街那面,盖了一排二层楼的房子出租来得到点收入。
另外,他很重视给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提职称的事,特别是给几个老先生,像彭泽祥,张鹏云二位老师提教授。彭老师的植物分类学,在我们西北都是数一数二的,精通得很。他教过我们的植物分类学,讲的非常生动。可是他的著作很少。张鹏云老师也是文章较少,但学识非常渊博,功底深厚,他教过土壤学,遗传学、植物学、植物地理学等等。这两位老师在科研发表文章上非常拘谨。虽然他们的文章不多,但在全国学术界很有知名度。为了他们两位提教授,王勋陵跑到校评委会给评委们、领导们宣传,抱了一大摞《中国植物志》说,虽然这不是彭老师编的,但是你们看,《中国植物志》编委竟然请的彭老师来修改,注释各处的对错,怎么订正,有这样的水平。于是就说动了评委会。可见王勋陵对老前辈的崇敬和他的热心了。
说起我们彭泽祥先生,他是个纯粹的学者,不太跟人打交道,他讲植物分类学。这门课描述性很强,很难讲好,可他讲的特别生动,很能叫学生把握住要领。我们班很有几个植物分类学学得很好的,有的分到科学院植物所、林科院的,后来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王:彭先生还把他收藏的国立兰州大学的校徽都捐给我们了。两枚三角形的校徽,1946-1949年的,上面写着“国立兰州大学”。
贾:是吧!退休后彭先生的余热仍在发挥,不断有人向他请教。他应该多带几个学生。 张鹏云、彭泽祥二位都是孔宪武先生的得意门生,孔宪武先生曾是甘肃省仅有的两个一级教授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他们都是师大的。师大在那时候的植物分类学在全国很有地位。

1986年贾敬芬在实验中
王:您和王先生怎么认识?
贾:王勋陵比我早毕业一年,我当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助教了。他和生物系几位要好的研究生住在一个宿舍,来来往往就熟悉了。他乍一看老实死板,但后来发现他也不是这样。虽然吹拉弹唱都不行,但是爱好还挺多,喜欢运动,会游泳,滑冰、滑雪什么的。
王:王勋陵的诗写了那么多。当时就应该表现出来了吧?
贾:噢,他还爱写诗,他学生阶段写的诗多,到后来忙了也顾不上写。那诗多半是学生时代写的了。他还爱写科普文章、还是科普作家协会、旅游协会的会员。他走到哪里,都爱看庙里的题词,关注各地的历史、地理、文化。他对古文也感兴趣,对古农学方面也感兴趣。因为他舅舅是学历史的,他是在舅舅家长大的,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他在学生阶段爱帮助人,谁家困难悄悄地给人家里寄钱,所以当时说他学雷锋学得好,其实就是一种本分。他对家里人也都是很诚恳的。他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喜欢他。都觉得他能吃苦。王勋陵有个姨姨,一辈子单身,王勋陵工作以后,一个月工资六十二元,就给在四川的姨姨每月寄二十块钱。后来接到兰州一起生活,直到养老送终。他对待这位老人,我看还胜过父母。
王:王先生也是一个善良的人。昨天听大家讲,王先生在学术上也是很成功的,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还推动了很多工作的前行。
贾:我觉得他有创新意识,爱标新立异。植物解剖学是一门描述性的传统基础学科,要搞点创新是很难找到突破口的。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的结构,都是自然存在,多以描述为主。现在新技术手段这么多,怎么能不做到墨守成规,有点新发现,该立什么研究方向?他经常和陈庆诚先生讨论这一问题。
在文革后期,针对西固的化工厂排放的烟雾,严重污染环境,他就和陈先生一块多次到西固去做调查、分析。他们首先发现兰州市存在严重的光化学烟雾,这在我们国家是最早发现光化学烟雾的存在。后来的立题是根据光化学烟雾开展工作,研究它对植物、特别是对农作物的危害。这些课题中,大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氮、臭氧对植物的影响,还有紫外线UV-B影响的研究方向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好多是这方面的工作。多年的研究积累,写成了《植物形态结构与环境》、《生物指示学》等著作。他在技术上曾做出了一点小发明。为做显微镜观察,传统的制作植物切片,很费时间,材料从固定、包埋,切片,然后到染色等等,要花好几天时间。他与徐永平合作,设计了一种植物制片仪器。他们设计的仪器,这一过程几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在当时还申请了专利。就把技术转给了一个工厂,还生产了一批,卖给了一些单位。这还真是一项成果。虽然工厂方面也没给多少转让费,当时也没那个概念,只要能给社会作贡献就满足了。
他在科研思路上把形态解剖学与生态学联系起来,立了不少课题。几位研究生做着生态解剖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研究西北荒漠地区的植物、形态解剖特征与环境的关系。
王勋陵推进的,有关大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氮、紫外线、微波、臭氧等,对植物影响的课题,后来被他的弟子们,如安黎哲的研究团队,西大岳明的研究团队,云南农大李元领导的实验室,山西师大韩榕的学科组,都还进一步做着细胞和分子机理以及污染防护方面的深入研究。
情深义重
王勋陵让人感到很严肃,但是个很善良的人。他的弟子们非常爱戴他。在他生病期间,临终前,四十多个弟子跑到西安去看望他,病床前照顾他。他去世以后,学生们把对他的那种爱戴深情都倾注给我了,经常地向我问寒问暖,关心我,路过或专程来看我,逢年过节给我发短信慰问,使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王:那你们也是对学生好嘛,你们关心人家,人家还是记着呢。
贾:这些学生们真好。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教授了,已是岗位上的学术骨干,带头人,都是大忙人,这么多年了还是情深义重。
我校虽然有一个民族研究所在人文科学方面进行研究,但还没有结合少数民族做些遗传方面的工作。王勋陵不是搞遗传的,但他想到,我们甘肃省有四个特有少数民族,就想到立这一方面的课题。由研究生谢小冬、杨亚军等人具体工作,现在这个方向的研究进展很好。由谢小冬领导的研究团队的工作已经成了大气候。杨亚军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也进行民族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很有活力。
王: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贾:是。把民族基因组学跟西北民族学研究结合起来了。
王:这也是做西部文章,西部的少数民族嘛。
贾:是啊!
王:那人家有这个创新头脑。他好像后来身体状况不太好?
贾:得了癌症。淋巴腺癌。他多年来身体实际上非常不好。从年轻时候就得了鼻窦炎,呼吸不通畅;到晚上口干舌燥,引起头昏,睡眠质量不高,后来肠胃也不好。他非常不注意身体,哪里不舒服还不跟人说,有病扛着,一直到发低烧了,才去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查。那个医院名气大,仪器精良,可是人山人海地挤,光检查就花了十多天。这个十多天等结果,没有任何医疗措施,只给点小药维持,病情不断加重。还要做脊背穿刺、肠镜检查、胃镜检查,真受了很大的罪。最后做第二次B超,夏天房间里开的空调,大夫们都穿的白大褂,让他敞着胸做检查,就感冒了,引发呼吸系统感染,心肺功能衰竭,他太弱了,光这个感冒就抵抗不住。当时就打算好一点了回兰州来,这里学生多,他也有在肿瘤医院工作的学生,最后还是因为白血球太高,又发着烧,根本不敢上路,就没过来。
王:当时年龄是?
贾:68岁
王:68岁这是哪一年?
贾:2004年。
王:噢,刚十年。哎呀,老先生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弟子满天下,学术成就又这么好。
桃李成蹊
贾:我在兰大1985年就开始招博士生了。当时郑先生是博导,我是副导师。招的第一个博士生叫许耀,是西北农大硕士毕业后到这儿来的,非常有钻研精神,实验室的条件简陋,但他能让其发挥最大作用。原生质体培养、体细胞杂交,遗传转化他全都做了。在这儿完成了好几篇文章,登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生物工程学报》上。毕业以后到中山大学做博士后,做博士后期间,继续做遗传转化,基因工程方面的工作,留在中山大学工作,获得了多项科技奖励,还被选为国家教育部跟踪的青年优秀人才。现在在美国,工作也很出色。
第二个博士生是西北农大年轻教师何玉科,我也是作副导师。他在荷兰瓦格宁根农业大学进修过半年多。我们是1987年在荷兰那儿开学术会议时认识的。当时根据在职人员申请的政策,他申请我们这儿的博士学位,参加了我们这里的考试,有了在荷兰的工作基础,深入作了油菜遗传转化方面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去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很快成为那里的学术带头人。现领导着一个学术团队。
到了1991年以后我就作为博士生导师招博士生了,每年都招几个博士和硕士生。这期间也还有一些郑先生的研究生,多做原生质体培养,体细胞杂交、突变体筛选和遗传转化方面的工作,像现在在海洋大学的唐学玺,在吉林的郝东云等,也都在我的实验室完成他们的实验。每年除带博士和硕士生外,还带本科生毕业论文。另外还有好几个进修生。实验室不大,但人很多,很热闹,很融洽。我在这儿指导过的博士生、硕士生,有二十五六个,大部分都很优秀。像蒋争凡,获得硕士学位后考上了北大翟中和院士的博士,他现在是北大的教授。硕士生赵忠,后来作复旦的博士生,现在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科学院的百人计划。还有徐子勤,在兰大时做体细胞杂交很成功,基础很扎实。现在在西大,也是那里的学术骨干,他的研究生们很佩服他,认为他是个踏踏实实作学问的,有真才实学。他前后花了八年时间,写成一本八十八万字的著作-《功能基因组学》,科学出版社出版,相当不错。
我到西北大学已经快20年了。在那儿组建了陕西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结合西部大开发和陕西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着植物抗逆境基因工程的应用基础研究,细胞与基因工程产品开发以及糖生物学与糖工程方向的研究。近年已从国外引进了好几个优秀人才,人员已经扩大到20多人。我在西大前前后后也招了20多名博士和硕士生,毕业后工作在全国各地,从事着教学、科研或开发研究,在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带头作用。我和他们都经常保持着联系。
在调到西大后的前几年,我还在兰大有三届研究生在读。侯岁稳教授现在是兰大生科院的博导,是我离开兰大那年才招的博士生。所以去西大后好多年里,我是经常回来的,直到他们都毕业了。
王:请您给我们留言。
贾:好。(写)插柳之恩永不忘。祝母校事业顺畅,越办越好。贾敬芬2014年10月20日
王:谢谢贾先生。
【人物简介】

贾敬芬, 1938年5月出生于河北深泽。196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植物学专业本科,1965年兰州大学细胞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67-1970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1年1月-1996年7月年在兰州大学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工作,期间于1979年10月至1981年10月曾在瑞士巴塞尔Friedrich Miescher 研究所作访问学者,进行植物细胞遗传操作领域的研究。1996年8月至今为西北大学教授,博导,组建了陕西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并担任实验室主任,2014年退休。历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四届副理事长,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两届委员。国际植物组织培养联盟会员。曾担任[实验生物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编委。研究方向为植物细胞工程。已培养博士生23人,硕士生25人。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以及省级科研课题三十余项。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参加编写著作10本。其科研成果曾获1987年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获省级科技进步奖四项,省教育厅科技进步奖7项,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两项。1989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92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自1991年7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陕西省人事厅和教育厅授予“优秀博士生导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