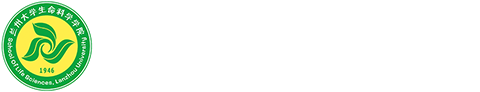在刚刚过去的8月,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马妙君带学生在甘南州玛曲县曼日玛乡科考时,路遇一位僧人。
闲聊时,僧人听到马妙君等人是兰州大学搞研究工作的,颇有感情地给马妙君等人讲了30年前他在当地遇到的几个人:“他们骑着马到我们寺院里,住了大概一个月,每天背着一个大箱子到沼泽湿地里去做实验,他们就是兰州大学搞研究的”。僧人会的汉语不多,但对“兰州大学”几个字,他却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校老一辈著名生态学家陈庆诚、张鹏云、彭泽祥、赵松龄、王刚等人就开始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寒草甸、沼泽湿地开展科研工作。
1992年,在青藏高原东部(海拔2700-4200米)、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杜国祯教授建立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甘南站) 。发展至今,甘南站施行“一站多点”的管理和运行方式,包括玛曲阿孜站、合作观测点,以及哇乐卡观测点,占地面积133公顷,成为集科学研究、教学实习、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服务为一体的实践基地。

2004年6月,即将本科毕业的马妙君第一次来到了甘南站做实验,尽管他从小生长在与甘南州相邻的临夏州,但之前也从未踏足过。
犹记得在前去的路上,同行的师兄向他如是描述甘南草原的美景:“就像WINDOWS XP 的桌面一样,蓝天白云绿草,特别漂亮。”
果不其然,他到达当天便见到了这样的美景,“天特别蓝,草地又湿又绿,尤其是在采样地看到了一个小山坡,真的和电脑桌面一模一样,就觉得生态学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学科。”这让他忽视了师兄让他出门要戴草帽的温馨提醒,第一天采样回来后便开始皮肤发疼发红、几天后开始脱皮。尤其是在经历了第一次刚才还阳光刺眼、顷刻间便暴雨倾盆、荒郊野外无处躲藏而浑身上下湿透的狼狈之后,马妙君感到生态学和之前理解的“好像还不太一样,梦想被浇灭了的感觉”。
而这样的经历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在甘南草原上做研究工作的导师杜国祯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从小生长在甘南草原的杜国祯不存在马妙君那样第一次踏上甘南草原的欣喜若狂,但现在已60多岁的他也同样记得在甘南草原做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有关草地生物多样性的”。

1992年博士毕业后,杜国祯留校任教,他萌生了建立野外实验台站来支撑在甘南草原继续开展工作的想法,“甘南重大的生态意义和独特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是我们兰州大学生态学应该抓住的优势资源。”
他的想法得到了张鹏云、赵松龄等一些前辈老师的支持,但同样也遭到了来自同仁和领导不同程度的质疑、反对甚至嘲笑:“杜国祯在那荒郊野外的建个站,不知道能干个啥。”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建站的决心。
在我国“两屏三带”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屏障。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甘南入境甘肃,而后在甘南玛曲绕了433公里后又回到青海,在这里形成了黄河第一道湾,在玛曲形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使甘南草原成为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高寒草甸的面积占到青藏高原的49%,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
对于该区域的高寒草甸和湿地退化后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马妙君如数家珍:会使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遭到破坏;会严重影响黄河上游的水源补给功能;会成为黄河中下游沙尘暴和荒漠化的源泉;会使泥炭中的碳大量排放出来形成二氧化碳、进一步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会关系到这个多民族交汇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生态学研究应该坚守住的阵地”。

从兰州到甘南州玛曲县有400多公里,对于现在前往的马妙君而言已经不是大问题,“自己开车或租车半天时间就到了,再到玛曲实验站的话当天也能到。”
而在1992年杜国祯建站初期的时候,路程远且交通不便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首个问题,“从兰州坐一整天班车到合作,从合作再坐一整天班车到玛曲,再从玛曲再往乡上或实验场地走就没有班车了。起初那几年是骑马下去,从玛曲到实验场地得走两天。后来就是自己联系当地单位的车,一般要等个三五天;运气好的时候碰上个兰驼拖拉机,跟司机商量好付点酬金就把我们带下去了。”

住宿同样是问题。从最开始租牧民的冬窝子、自己搭土棚子、搭帐篷,吃的是山泉水、照明是太阳能电池板发的电,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到后来租当地单位的平房,再到现在拥有甘南站自己的房屋,杜国祯一点点让所有问题都变得不是问题。“像我在甘南站做工作的时候就非常幸运,只住了一段时间的帐篷就住到房子里了,在这方面杜老师真是费了心血”,马妙君说道。
相比生活条件保障上的坎坷,经费的短缺是甘南站发展的最大制约。“建站初期经费支出最大的就是给实验场地修围墙,没有围墙的话种的草很容易就被牲畜破坏掉,实验就白做了。因为雨水充沛,围墙大概两三年就得推倒重修,在90年代修一次大概需要3万多块钱,钱主要花在这上面。再就是买些简单的工具,例如天平、卷尺、纸笔等。”即使这样,刚开始甘南站的运行经费要么靠杜国祯自己垫钱,要么用其他科研项目的经费,甚至他两次将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共将近30万投入到甘南站的运行中,到后来渐渐获得了学校的经费支持,这才使甘南站的生活设施、实验条件等有了大的改观。目前,甘南站已经拥有总建筑面积1720平方米、生活设施齐全、可满足一百余人长期住宿需求的房屋,拥有价值2000多万的监测草甸和湿地的仪器设备。

甘南站在杜国祯的带领下逐步走上正轨。
2011年7月,甘南站扩建升级为“兰州大学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农林实践基地——高寒退化草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广基地”。
2011年9月,甘南站作为亚洲地区唯一进入营养物研究网络(Nutrient Network,简称NutNet)的野外工作台站,参与观测的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在全球知名科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
2012年,甘南站被学校正式认定为实体科研机构。
2018年,甘南站被甘肃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台站。
2019年,甘南站被教育部认定为部级台站,与“甘肃庆阳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一道实现了兰州大学部级野外台站零的突破。
如前文所述,甘南对我国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和过度放牧,甘南草地严重退化、湿地面积萎缩、次生裸地过程加剧、水源补给量减少,草地的水源涵养、补给的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已严重受损,成为我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合理利用不同类型的草地,通过何种措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提升草地水源涵养功能、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实现生态系统稳定、草地可持续利用、草地畜牧业良性发展,这已然成为该区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杜国祯团队围绕这些问题,通过长期的基础研究和积累,进行了大量的高寒草甸和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恢复机理研究。
进行了低耗高效水分利用植物建植技术研发,在积累的近30年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高寒草地与湿地毒杂草和高耗水植物危害的中、长期预警方案,建立了一系列技术体系并示范应用。
根据高寒沼泽湿地植物群落结构及主要组分种的特性,以退化湿地植物群落关键指示种的繁殖物候为标志,首次提出了以植物物候特征为关键指标的、适用于高寒湿地的中长期预警技术。
提出高寒沙化型次生裸地治理技术。提高了沙地植物褐鳞苔草种子繁殖和地下茎段繁殖成活率(达到80%以上);研发了不同尺度的山生柳网格状高寒沙地固沙技术,效果显著。
提出高寒草地利用模式。通过调控放牧单元尺度、调整放牧时间有效地减轻了草地承载压力、牲畜死亡损失,利于牲畜换季健康及牧民生活,是全国草地承包到户后草地保护性利用及退化草地、湿地恢复行之有效的创新模式。

界定了高寒草地适宜载畜量,构建了以植被盖度为基础的草畜平衡模型,确定了玛曲草地过牧的黄色和红色预警系统。
提出高寒草牧区草畜平衡方案。首次制定了以人-草-畜平衡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减畜方案,该方案是甘南州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提出基于GIS技术的玛曲降水资源调控集成业务应用系统。系统研究了玛曲降水气候背景、水汽来源及通道,给出了适宜人工增雨作业的天气系统、云系特征及作业催化的部位、时机选择的依据。
针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功能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甘南站从学科发展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国家需求出发,瞄准国际生态学研究前沿,经过长期的积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截至目前,依托台站发表论文431篇,其中在Ecology Letters,Global Change Biology,Ecology,Journal of Ecology,New Phytologist,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等生态学主流期刊发表SCI论文163篇;发表在著名期刊Journal of Ecology(2篇),Oikos,Behavioural Ecology,Plant and Soil 的5篇文章被选择做封面文章(Editor’s Choice)。通过国际合作,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在自然科学顶级杂志Science发表2篇,在Nature发表3篇论文。

基于上述研究及成果,2009年,杜国祯作为首席科学家,针对草地退化、湿地面积萎缩、黄河水源补给量减少等严重的生态问题,成功申请到支持经费1765万元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该项目的执行收获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区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使得整个项目实施区域高寒草甸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水源涵养功能大幅提升,对玛曲的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重要作用。项目成果示范推广后,应用退化湿地生态系统修复技术,草地综合生产力可增加30%以上,示范区内平均每公顷可增加鲜草产量1400公斤,推广区按示范区增加鲜草产量一半计算,每年可增收900多万元。通过建植人工草地,906亩实验区每年可增收近50万元。次生裸地采用植被重建、补播、施肥等多种措施治理后,可使牧草产鲜草产量提高52.6%,并培育山生柳苗木30万株,次生裸地示范区每年直接经济效益近500万元。通过畜群结构优化,实施草畜平衡方案,提高出栏率及增加冬春补饲,不仅增加了牧民收入,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牛羊的死亡率,使冬春家畜死亡率降低了2%,玛曲县牧民每年可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所开发的草原观光、特色民族文化、有机特色产品的品牌效应等潜在项目的开发将会给当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长远经济收益。

在项目支撑下建成1个示范基地、5个示范区,共培养研究生77名、专业技术人才45名、牧户200余名,为当地培训了一批技术推广人才及牧民技术能手。通过示范牧户和技术骨干调动牧户科学管理利用草地的积极性、增强其生态保护意识,实现人草畜和谐发展,进一步提高了青藏高原牧区的整体生产科技水平。使草地利用更加合理,遏制草地退化所造成的损失,减少有害生物防治、次生裸地治理等方面投入,调整畜群结构、增加出栏率结合冷季补饲促进了草畜产业的良性循环和发展,促进地方经济高效发展。
2014年,该项目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之后杜国祯提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是青藏高原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
首先,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可以尽快地降低青藏高原牲畜的数量,减轻畜牧业对天然草地的压力,达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之目的。
其次,生态文化旅游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并不需要复杂的专业技能,工作时间与地点相对灵活,投资回报的周期也较短,可以使牧民较快提高现金收入。
再次,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并不是不发展畜牧业,而是将其作为旅游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青藏高原黑白镶嵌、高矮错落的成群牛羊构成的壮美景色是其无可替代的旅游资源,藏族传统的住黑帐篷、骑马等生活方式可以开发为有品位的旅游体验活动,牦牛肉、酸奶、藏毯等畜牧业的产品作为旅游产品销售具有更高的附加值,游牧生产活动及其产品也会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宣传也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牧民的收入与视野提升之后,会逐渐结束依赖于天然草地的生活,主动选择到学习、生活、医疗条件更好的乡镇、城市去生活,从而激励主动的生态移民,更有利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建议报告于2017年6月得到甘肃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批示。之后,甘肃省不仅摘除了甘南州在GDP目标上的“紧箍咒”,而且通过修建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对于生态学领域的经典问题、冷门问题,杜国祯也锲而不舍,“科学研究就是要抓住学科的本质问题、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
2004年,马妙君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杜国祯便给其指定种子库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对于这项自己完全不懂的研究,马妙君深感不解,“土壤种子库,听起来像到哪个仓库里工作一样,所以说非常冷门。冷门学科的直接体现就是不好出成果、不好发文章、不好毕业,当时作为学生,首先考虑的还是发文章毕业的事情嘛。”但马妙君还是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和安排。
什么是土壤种子库呢?每一种植物母体成熟之后都会孕育出很多种子,种子个体会因为风吹、鸟衔等原因扩散,最终落到土壤里,其中一些种子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出来,而更多的种子存在了土壤里面,如是日积月累,土壤里留存了大量各种植物的种子,既能反映植被的历史,也能预测植被的将来,即土壤种子库。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采集土壤里面的种子,辨别这一区域内种子的种类和数量,并分析该区域土壤种子库在植物群落更新和退化植被恢复中的作用。例如,某种植物在某一区域地表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分析出其土壤中是有这种植物种子存在的,那也就是它有生长出来的可能性,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改善土壤环境等其他因素来促进其生长;如果某种植物在地表上不存在、土壤中也没有种子,那么就要补种,补种的投入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能研究证明这个区域里有这种种子并且它可以萌发出来,那么不就免去了补种的高投入嘛。”
采集种子的工作就是这项研究中碰到的首要难题,“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要采集几千粒甚至上万粒种子,采集工作每年从8月开始一直到11月,全靠人力,所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种子采集回来后,先晾干、然后在4度的环境下保存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它更有活力地保存下去,另一方面是模拟大自然当中的春化作用。春化作用就是所有的大自然中的种子经过冬天的冷冻、春天才能更有利地萌发。”第二年春天再做萌发实验,通过此研究种子的萌发特点。截至目前,杜国祯团队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拥有700个物种的种库。
在这条研究路线上,马妙君坚持做到了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马妙君提出想改变研究方向,“毕竟这个做得人又少,工作量又大,出成果太难了”,但杜国祯坚持鼓励他继续做下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国祯的坚持没有错,马妙君也不负厚望做出了一定成绩,于2014年被聘为学校的青年教授,“当时我才31岁,这个对我的鼓舞太大了,一下子有信心了,就想着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做出点成绩来。”
2019年,马妙君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更是对他这些年工作的莫大肯定。
对于这一切成绩,马妙君无不归功于导师杜国祯。

慈祥、严厉、简单,这是马妙君眼中的杜国祯,但最让马妙君受益的还是“杜老师那种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劲头和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团队、我们台站得以长期传承下来,这也是我们台站今天取得这些成绩的最大源泉”。
从建站之初每年在站上常住大约半年时间,到后来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每年也能在站上呆两三个月时间,杜国祯始终没有离开甘南草原这个工作平台。“在站上一方面是指导学生开展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是和当地的政府、牧民等协商解决租用草原、房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在站上,我不仅是他们的老师,更是他们的家长。”
2014年至2016年青藏科考,时年已近60的杜国祯坚持带着学生们奔波在青藏高原上,每天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回来,回来了整理样本到半夜,中午就在草原上喝矿泉水吃白饼榨菜。
长年累月的野外奔波加上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使杜国祯的身体发出了超负荷的信号。2016年11月,正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杜国祯胃部剧烈疼痛,他坚持了两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得提前离会返回兰州,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胃癌。很快他便接受了手术,切去了三分之二的胃,休养了大约半年后,杜国祯又返回办公室,“还有学生的毕业论文等着我看呢”。
在杜国祯的示范带动下,从过去条件极其艰苦到现在条件相对改观,在应该从事野外实验、野外考察的季节,他的学生总是毫不犹豫地外出,“学生看老师是这样做也就没有怨言了,师弟师妹看师兄师姐是这样做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因为吃不了苦而放弃的学生”。

相反,杜国祯及其他老师依托甘南站培养了博士80余人、硕士200余人,其中一些已经成长为国内生态学研究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例如中山大学储诚进教授(国家杰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武高林研究员(国家优青)、南京大学牛克昌教授、兰州大学张世挺教授、赵志刚教授等。现为生态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的赵志刚教授也在2017年成功牵头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川西北和甘南退化高寒生态系统综合整治”,中央财政支持经费1838万,成为自国家科技计划新政策实施以来我校作为牵头单位获批的首个重点研发项目。
而杜国祯对马妙君唯一一次的夸奖,也心有灵犀地强调了马妙君的坚持,那是在2017年11月13日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党支部召开的讨论接收马妙君为预备党员的党员大会上,他称“马妙君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可爱在什么地方呢?野外工作需要坚持,坚持一个科学问题,坚持一种勤奋的精神,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谈起入党一事,马妙君也由衷地感叹“入党动力来源于团队的精神传承,杜老师就是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老师们的感染带动下,团队学生入党比例也非常之高,“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大概有90%是党员,剩下10%也正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2018年,马妙君接过了杜国祯的接力棒,承担起了甘南站负责人的重任。对甘南站的未来,他目标明确:在现有的基础上,建成一个硬件设施进一步提高、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实现天地空全方位监测的开放化实验站,“将来在国际上生态学研究领域有我们一席之地,能吸引到全世界的科研人员到甘南站来做实验”。宏伟目标的背后是忧心忡忡:“杜老师建站的过程非常不容易,我很担心自己不仅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反而把站搞砸了”。
而谈到对甘南站未来的期待,杜国祯表示“就希望年轻人不要赶时髦、瞎折腾、乱搞创新,就抓住生态学的本质问题,稳扎稳打地往前走”。
原文链接:http://news.lzu.edu.cn/zt/ddh2020/72486.html